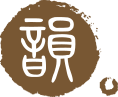书房是读书人的一隅,家有书房那将是读书人增长知识,修身养心,快乐放松的一阁。我的书房并不大,仅能容纳一排四组书柜,书柜是欧式的,书桌和茶几靠背椅是中式的,也算得混搭中西合壁。书柜的三分之一是藏书籍,主要是集评弹、戏曲和吴文化方面的书籍;三分之一是藏书画册,主要是集吴门书画家的册子及作品;三分之一是藏音乐“书”籍,主要是集评弹、戏曲的音频、视频的珍贵资料。
弹丸方寸怎能藏得下我的藏品,书房之内则是我信手拈来的常用之宝而已。
从小就喜欢本土文化的我,对苏州评弹情有独钟。在家就会走进书房坐在书桌旁,背靠着藤椅倚望着一本本书本,他们都是我的益师良友,读来既熟悉又陌生,传授给我知识,传递给我信息,让不出门的读者了解苏州的历史与文化。姑苏这方水土滋润着苏州人的秉性与涵养,催生孕育了苏州评弹、昆曲和吴门书画等等,虽说艺术种类不同,但它们一同展示了吴文化的温润、典雅与精细,折射出吴文化独特的艺术品位。评弹成了我一生的钟爱,于是凡看到与评弹有关的书本、即便内部刊物资料也总要想方设法弄到家,《评弹通考》《弹词叙录》《评弹散论》《评弹艺术家评传录》《苏州评话弹词史》等等,一本本一行行列进我的书柜,天天为伴。日久天长,注重学习坚持积累,在我的书桌上写出了一篇篇文稿,如《徐云志情趣琐事》《吴子安的半回捉鹦哥》《严雪亭假刀吓妻》《五见蒋月泉》等等,前几年这些文稿汇总出版了一本题为《评弹情缘》自己的书本,算是我书房中的积累所出的果实吧。
书房一般用来看书写字,我却有闲趣在书房听书。何谓听书?此“书”非那书,苏州人讲听书即是欣赏评弹也。听书实在是一种很幽静放松的感觉,说书先生语言诙谐幽默,外插花噱头让听者想笑,肉里噱听了哪怕喝口茶之后想想还要笑,有回味感。评弹(弹词)中的弹唱也是静笃笃的慢条斯理,一曲三弯,余音绕梁,评弹唱腔讲究的是韵味。若在书房内放上盆栽荷花,放上一曲《莺莺操琴》,借着窗外射进的一缕阳光,醇厚欲滴的弹词唱腔会让你沉醉在情不自禁的意境中。有人说音乐是不分国界的,别小看评弹小曲种,难道只有苏州人江南人喜欢她吗?不,美国学者马克·本德尔、日本学者石海青(中国名)、黑田谱美、荷兰学者高文厚(中国名)分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和近年来都走进了我的书房,我们一起听书共同探讨,国外知音成了我的书房之友,可谓“知音觅知音”。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,评弹之美,美在你我他的心中。
苏州评弹与吴门书画有着异曲同工之美,含蓄、秀美、精致、细腻相当耐听耐看,这是著名吴门画家潘裕钰常说的话。我和潘老师兴趣相投,评弹、书画两相宜,我俩在书房交流,我赠他评弹藏品,他送我绘画作品,以书为友。也常有三五好友来书房而一坐,赏曲品画,都是以评弹题材的书画,如潘裕钰的《玉蜻蜓》、王锡麒的《莺莺操琴》、张晓飞的《陈采娥赠塔》、李大鹏的《百年传承珍珠灿烂》……
在书房看书充实了我胸中的知识,在书房听书提高了我的艺术素养。看书听书拓宽了我的眼界,找到了我的创作灵感,在书房中创意、构思、策划的电视评弹、昆曲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,观众的好评,获得了全国大奖,这些动脑瓜的工作与我的看书听书是密不可分的。
我与书,我与“书”成了知音,故而我曾为书房起了小名“知音阁”,后来又有文人说你看书如渴,书比泉,听书就似清泉溪流美妙如此,书法家费之雄先生由此为我题写“聴泉阁”,我乐在其中。